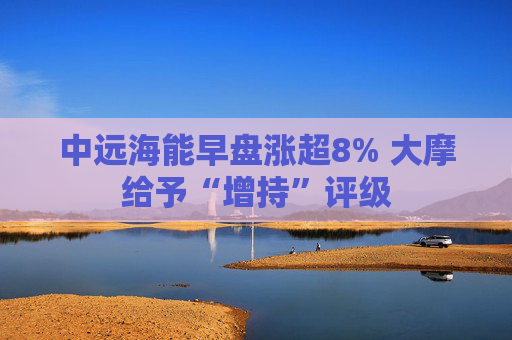李良荣:难忘的一面之交
- 每日科技
- 2024-09-17 11:33:30
- 17
中秋思故人,千里共婵娟。年近八旬,一生中与之交流的人很多,有些成了终生之友,有些则渐渐淡出,就像在人群中,走着走着,有些人就走散了。而在各种场合,偶然遇见的人难计其数,随见随忘。但却有几个人,不知其姓其名,偶然的一面之交,在瞬间所绽放的人性的光芒让我感动不已,像历史性的镜头定格在我脑海中,在某个时刻,在某个场景中,一次次重新展示在我面前。
卖桔子的小哥
1992年9月中旬,全国新闻教学研讨会在宜昌召开,我当时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应邀出席会议。会后主办方组织我们去巫山县游览三峡。
我们一早出发,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大巴一路颠簸,临到中午才到大宁河边的游客集合地。简单午餐后,大家集中在游船入口处。这个入口处摆着很多售卖当地特产的地摊,其中最多的是卖当地产的桔子,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好生热闹。因为离开船还有些时间,我信步走去看看。那十几个卖桔子的摊子已围了不少游客。看到边边上有两个桔子摊前面没人,我就走过去看看。摊前有一老一小一年轻人,看上去像祖孙三代。那名老妇人头发花白,至少六十岁了,我称他老婆婆。那名小孩五六岁的样子,依偎在老婆婆身边,嘟嘟嚷嚷着,看到我走近才嘟起小嘴不说话。那位青年看上去三十上下,满脸黑红,满头大汗,穿着一件已褪色的藏青色中山装,肩上两块大补丁,胸前也湿漉漉的,看上去像挑着担子赶了不少路。他们面前摆着三筐桔子,那名青年人面前有两大箩,估摸四五十斤的样子。我猜想他们一家子赶了不少路,老婆婆也自己背了几斤来卖。但老婆婆那一篮的桔子却明显要小一些,价格倒是一样的。我就让那名青年称五斤,准备到船上给同来的老师们分享。但那名青年一本正经对我说:“你买婆婆的吧,虽然小些,但更甜。”这名青年看上去很质朴,我立马信了,以为桔子大小是有不同品种,小些但更甜也有道理,就买了那名老婆婆的桔子。称好,付了钱,老婆婆满脸堆笑,连声致谢,领着小孩走了。小孩欢天喜地,蹦蹦跳跳喊着:“买棒棒糖去啦!”

待到大家上了游船,我把桔子摊到桌面上请大家品尝。自己先尝了一只,甜是甜的,但还有点酸,桔子显然没熟透。同行的老师们吃了,还是赞扬说“蛮好吃的”,我也挺高兴。谁知不一会剧情就变了。有一名老师把买来的桔子也摊在桌子上,大家一吃,立马评定:他的桔子比我的好。我剥开一只尝尝,确实,他的桔子个头大、皮薄、汁多,更甜,没酸味。一问价格,都一样的。那位教师说:我前脚买了那名老婆婆的桔子,他后脚就买了年轻人的桔子,还说:“我以为你识货,就跟着你买的。”引起大家的哄笑。我感觉自己上了那名年轻人的当,心中有些不快,但很快就被小三峡的壮美景象吸引,此事便抛在脑后了。我们的游船沿着马波河逆流而上,几处激流险滩,船头激起几米高的水花。两岸青山绿水,还看到三两猴群迎空鸣叫,尤其是导游指点我们看那位于悬崖峭壁间栈道的遗迹,令人感叹先民们筚路蓝缕,开拓之艰辛。
游览时间并不长,两个小时左右就回到大巴车集合地。下了车,我一眼就看到那名年轻小伙子,还是在原地卖他的桔子,所剩已不多了。我走到他面前,笑嘻嘻地问他:“你哄了我,是吧?”我避免用“骗我”这词,那名年轻人也认出了我,立马涨红了脸,但不回答我。
我又问他:“那名老婆婆是你什么人?你老妈?亲戚?还是邻居?”这下他有点急了,“这位大哥,哦,不,先生”,他不知怎么称呼我,结结巴巴地说,“我真不认识那位老婆婆。她可能住在附近,我住在河对面的深山里”,他指着马波河对岸,“离这里有十来里路。”这让我更好奇了:“那你为什么帮她卖桔子?”他似乎看到我笑嘻嘻的,不像找他吵架的人,脸上的羞红这才褪下去,告诉了我原委。原来老婆婆的孙子看到人家吃棒棒糖,嘴馋了,吵着要找老婆婆买。老婆婆身上没钱,就摘了家里种的桔子来卖。但桔子品相不好,两个来小时没人买,孙子又哭又闹,那老婆婆只好央求小伙子,说便宜点,买下她的桔子。而小哥从山里挑了桔子刚刚到集市,身上也没钱。“那会儿刚好你来了,我就让你买了。”
“那你知道你的桔子比她的好?”我坚持问。
那名小哥不置可否,只抓起几只桔子,“你尝尝,我们老山里的桔子真甜。”
这时,广场上吹起上车的哨子。我说:“小哥,这剩下的桔子我全买了,快称吧!”
小哥怔了一下,然后动作利索地装上、称好,我付完钱,很郑重地对他说:“小哥,你桔子好,人更好,敬你!”
我转身走向大巴,临上车,回头一看,小哥还在那里,向我挥着手。
大禹陵里的僧人
我曾和绍兴大禹陵里的一名僧人有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接触,不知其姓、其名、何方人士,却终身难忘。
1967年春节后,学生们凭学生证可以畅游全国,免费乘坐交通,吃、住由当地政府全包。我们复旦大学10位同学组队从温州一路走到绍兴。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我们到绍兴的第一站当然是去参观鲁迅故居。鲁迅笔下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得那么令人神往,可到现场一看,我大失所望,因为在我的家乡,这样的菜园子随处可见,这座书屋也很平常。于是我急切地想着去拜谒大禹陵,大禹治水的传奇从小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从绍兴市中心到大禹陵十来里路,我们步行前往。一出城区,视野突然开阔,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正是早春二月,那天正好风和日丽,江南最美时节。我们一路前行,路上铺的全是石板,石板路两旁柳树刚刚返青,嫩绿的柳枝轻拂在我的脸上,不远处的油菜花黄灿灿的一片。尤其令我惊奇的是那条通向大禹陵的青石板长桥,架设在湖中,绵延数里。一阵微风,带来青草的清香,山雀的鸣叫,鱼儿的欢腾。这是春在吟唱。
伴随着一路欢歌笑语,我们走进了大禹陵。一入大禹陵,我们被眼前的破败、冷清惊呆了。大禹塑像已被砸烂,墙角处还堆着一些碎片,塑像的青石座基四角都砸断了,大禹陵的石碑也断成两片,只留下光秃秃的土墩。
我们一群人正小声议论着,从大禹陵旁的偏房里走出一名僧人。这名僧人中等个子,短发,清瘦,穿着一件宽大的僧袍,袍子上有好几块补丁。他慢声细语地说:“欢迎各位到来,请到房内小坐”。进到房内,房间不大,一张小四方桌,有个小灶,再里面用蓝布帘遮着小床。这是这名僧人的卧室间兼厨房,整个大禹陵当时就剩下这间房子还算完整,其余都已破烂。我们十个人围着小桌子挤着坐下。这名僧人给我们每个人倒了一碗水,然后从橱柜里端出两只小碗,一只盛着炒熟的黄豆,另一只里盛着小青豆。“各位请慢用”,他依旧细声慢语。炒黄豆、小青豆在当时还是难得的零食,我们一边吃一边问着大禹陵的情况。但这名僧人却不回答任何问题,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我们感觉他有顾虑,也不再多问。吃完豆子,我们每人拿出两角钱算作茶水费,交到那名僧人手里,想起身告辞。两毛钱算不上什么大钱,但在当时不能算小钱了。令我们惊奇的是,那名僧人轻轻地推开,不收我们的钱,却拿出一本小笔记本,缓缓地说:“各位都知道,大禹治水,造福民众,值得我们后人纪念。恳请各位在这个本子上签个字,请求政府重修大禹墓碑,重塑大禹像。”
我当时坐在最靠僧人的座位上,顺手就接过本子,看到本子上已有不少人签名。我觉得签个名是应该的,刚拿起笔,却被一名同学阻止了,悄悄对我说“万一出事,追究下来,说不清了。”听到“追究”一词,真把我吓着了,也不知道这到底会追究什么,只好讪讪地把本子还给僧人。那僧人不动声色,默默地把本子收起,放回抽屉。
回来路上,风光依旧,但再没有了去时的欢歌笑声。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只是都不言不语走着。我却像心头压着块石头,堵得慌。不知在想着什么,想说什么,只是默默无语,低头走路。那天晚上,睡在床上,闭上眼睛就浮现出那名面黄肌瘦的僧人形象。他不贪钱财,不怕担责,广集民意,坚持重修大禹陵。他那么虔诚,那么忠于职守,相比于我的胆小怕事,深深感到内疚。我当然知道,像我这样人微言轻的一名学生,签不签名对于重修大禹陵并无多大作用,但不敢担当、逃避责任,让我愧疚不已。
1989年冬,时隔22年,我再次来到绍兴,再次去拜谒大禹陵。大禹陵早已重修,金碧辉煌,游人如织。我想找那间偏房,想再寻找那名僧人,但破旧的偏房不见了,只有摆着沙发、铺着地毯的会客厅。穿着补丁服的那名僧人更无处可寻。
我向大禹像三鞠躬,仰望着,沉思着。一切造福于民的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凡人,不管是创造惊天动地伟业还是微不足道小事的人,都值得人们纪念。
临行前,我往功德箱里塞了一把钱,不是做功德,只是寻找自我安慰。
在火车鸣笛的那瞬间
1964年夏,我们复旦大学新闻系63级同学,由系里统一安排去各报社实习,我被分去《文汇报》文教部。那天,部里通知我随一名摄影记者到火车站采访应届高中毕业生奔赴新疆。去前,部主任交代我要现场采访一名市重点中学女学生(我记不清她的姓名,暂称女学生)。她是应届高中生,成绩不错,但她响应国家号召,自愿放弃高考,奔赴新疆,开垦戍边。受她感召,有一批应届女学生组成巾帼戍边排,在全市引起很大轰动。
那天,我跟随《文汇报》那位女摄影记者来到火车北站,事先已联系了北站一名工作人员,直接把我们带进站。站台上人山人海,喊声、哭声、絮絮话语声,一片嘈杂。赴新疆的学生都穿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黄色军服。北站那名工作人员领着我俩挤过人群,来到那名女同学前,我已全身是汗,衬衣被挤掉两粒纽扣,很是狼狈。这名女学生中等个子,梳两只羊角辫,红扑扑的脸上流着汗水。见到她时,她正帮她妈擦眼泪,说着“妈,不哭,我们说好不哭的”,他妈一边擦泪,一边说“不哭,妈不哭”。当工作人员介绍我是《文汇报》记者身份,我直接就提问她此刻的心情。或许她事先已知道还有记者采访,豪迈地对着我大声说:“我们即将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奔赴新疆。我们要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把新疆建设得像上海一样,请上海人民听到我们胜利的喜讯!”
刚刚说完,哨子声响起,“快上车,火车马上要开了!”站台上突然静止了几秒钟,又突然间爆发一片震天哭喊声。我身边几名妇女拉着孩子的衣袖,嚎啕大哭起来。那名女学生的妈妈倒很坚强,没哭,使劲拉拉女儿的衣袖,给女儿整理上装,送女儿上火车。女学生拉着妈妈的手,重复着“妈,不哭!妈,保重!”然后上了火车站,在车厢的台阶上,回过头看着她妈,我看到她泪流满面。
车厢门关了,突然间,火车鸣响汽笛,车轮缓缓启动,火车窗口伸出无数只手挥动着,挥动着。有几位男子追着火车,被车站工作人员拦下。汽笛声伴随着远去的火车,已被声嘶力竭的呼儿唤女声所淹没。那位女学生的母亲就在我面前一屁股坐在地上,指着火车的方向哭喊着。我看见几名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拿着担架往前赶,原来是有人晕倒了。
回到报社,我赶紧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报道,部主任表扬我,说那位母亲为女儿整理军装出征的细节抓得特别好,第二天见报,刊出三幅大照片,展示上海市民热烈欢送赴新疆兵团战士们的火爆场面。但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却是:在火车汽笛鸣响的那一刻,无数双在窗口挥动的手,女学生泪流满面回眸看着她母亲的那一瞬间。
金业缘之缘
2022年三、四月间,上海全城为抗击新冠疫情进行静态管理,我当时要去医院换药,持有医生证明,由居委会盖章放行,允许我每周可以外出两天,每次由我太太开车接送。无论去华山医院还是新华医院,整个街道空空荡荡,一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能偶尔看到几辆警车或货车。
那是四月中旬,我们开车从新华医院回家,一路很顺畅。经过国顺路政本路口时,我突然瞥见有一家水果店开着门。我赶紧对我太太说:“你停停车,有家水果店开着门。”我太太不相信:“你看走眼了吧?现在哪家店还敢开门?”但在我坚持下,车子还是停在离水果店200米的拐弯处。我走过去一看,水果店确实敞开着,五、六名工人正忙着搬运整箱水果。我怯生生地问门口一名年轻工人:“师傅,能否卖点水果给我?”他迟疑地看了我一会,说:“老先生,我们不对外零售。”我当然明白,当时规定所有店铺都关门,这家水果店如果卖水果给我,确实面临被处罚的风险。但我心有不甘,还是再次请他“高抬贵手”。
这时,一名中年汉子走出来,身板高大壮硕,满头大汗,只穿一件短褂,像是这家店的老板。他看着我们好奇地问道:“两位长辈,你们怎么出来的?”
我太太回答他:“我先生刚看好病,从医院回来。”
“噢,去看病啊”,他从店门口走到街上然后对我说:“病人是应该多吃水果。不过我只能整箱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你们带了现金吗?不可以微信付款的哦。”我是个老派人,口袋里习惯放现金的。我立马掏出几张一百元的给他:“没问题,我现金支付。”我要了两箱苹果,两箱香蕉,还有西瓜,哈密瓜。我们像是老鼠跌进米缸里,开心得不要不要的。我太太把车子开了过来,几名工人帮忙把水果搬上车。我突然发现店里还有刚上市的荔枝,喜出望外,赶紧又买了一箱荔枝,身上的近千元现金几乎都掏出来了。老板收了钱,催促我:“不好意思,请快开走吧。”我俩又像是叫花子捡到了金元宝,突然发了大财似地,边开车边在商量如何设法把这大笔水果财富分送给附近的学生。车子开了不久我又后悔了,感觉这一箱荔枝不够分的呀,我叫太太把车子开回去再买一箱。我太太怕我大病初愈累着了,说道:“我们的出门证明天还有效,明天去买吧。”
第二天,我们兴冲冲特地开车去那家水果店,却大失所望。水果店大门紧闭,从门缝处窥探,店内一片漆黑,看不到一个人。我后退几步抬头一看,才知道这店名叫“金业缘水果店”。昨天兴高采烈,竟没有看清店名。我记住了那家店,更记住了那位壮硕的中年汉子。
我们在叹息、无奈中回到家里,把水果分成多份。同一住所的邻居,就趁着核酸检测可以出门的机会,把水果悄悄地放到他家门口。附近的几家学生,我们开车过去放在他们小区门口的货架上,请志愿者帮忙送到他们家里。很快,我和太太收到许多带着微笑的信息,告诉我们,他们收到新鲜水果的惊喜。尤其有小孩,有老人的家庭,家里喜气洋洋。而我那时,最想告诉金业缘那位中年汉子:你的善举,给那么多家庭带来了笑声。
可惜,我不知他的姓与名,更无法联系上他。
(本文写于2024年中秋前夕,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