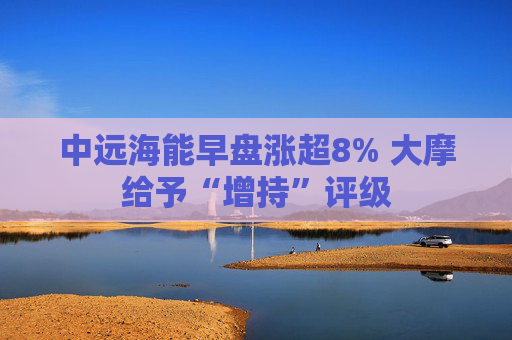文学派对|李少君自述:从《天涯》到《诗刊》,人诗互证
- 每日科技
- 2024-09-26 16:26:53
- 41
就文学而言,学院跟“修辞”或“学派”,媒体跟“热点”,其实都有点错失“文学的专业性”这回事。同时,文学内部正在以一种可能主流或整体未察觉到的方式产生并巩固其专业或专业性,比如胡安焉、李娟。总之,文学的专业性已经是很显在、很重要的时代命题了。在更加极变的当下,世界如何发生、意义如何生产、经验如何形成,是更加重要的。这可以称之为流动的当下。而自述刚好契合了用个人、作者自己的态度与想法应对这个命题。当然,使文学成为文学、使文学生成文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很期待像自述这样的“折返跑”给某种可能的未来建立一定的夯土地基。澎湃新闻邀请与文学相关的各行各业人士,写作者、翻译、出版人、文学杂志编辑、平台方负责人、编剧、读者等等,通过自述的方式,来谈谈文学。

李少君在《珞珈诗派》第二辑首发式上。李少君,诗人、作家,出生于湖南湘乡,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曾任《天涯》杂志主编,现任《诗刊》杂志社主编
回忆我个人的思想历程,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代中期是哲学的阶段,当时我对人生意义产生了怀疑,也正好认识了张志扬这批人,读了很多哲学书。在这个过程中,《天涯》创刊。《天涯》的品位符合我的理念,我开始参与《天涯》的工作。我主编《天涯》十年,学者们和批评家们大肆争论,讲的都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或者说他们的道理只是一方面的、一个角度的,并不是真理,但是他们个个都相信自己是真理。我回到诗歌和这种情况关系很大。
我后来得出结论,诗歌是最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相较于其他人更坚定地以诗歌为最高目标。我常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能使用文字。动物也有语言,但不会使用文字。人类有了文字,才有文明。最高的文字形式就是诗歌,诗歌最简洁、最符合我们的审美。人类追求的最高目的就是美,从文字的角度而言,美的象征就是诗。这是我通过人生经历得出的结论。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小说家、散文家称之为“家”,而诗人称之为“人”?我是这样理解的,诗歌是最突出作者主体性的文学体裁,诗如其人,人如其诗。人诗互证,人诗对应,人诗合一,既是古老的诗人之为人的意义,也是未来诗人得以自立自证的标准和尺度。因为,诗永远是人之精神印迹和生命证据。诗,一直最具个人性和独特性,也证明人之个体性和独特性。更重要的是,加强内在修养和境界的提升,要成为一个大诗人,要写出大作品,这一点尤其重要。
诗歌,既是个人情感史、心灵史,也是生活史、社会史。这也是“人诗互证”传统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原因。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保卫诗歌,需要以诗歌赓续历史文脉。
01
人生每个阶段我都是认真的、真诚的,最后我自然而然变成今天这样。大家特别推崇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人到了一定年纪慢慢体会。
2014年,我担任《诗刊》主编。《诗刊》是“公器”。从《天涯》到《诗刊》,刚开始有一段时间不太适应。在《天涯》时,想做什么基本都可以做,没有什么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自己决定就行了,只有个人任务要完成。我完全按个人喜好来办,不管你的名气多大,我不想发你的作品就不发,我不担心会有什么后果。到了《诗刊》,就不能这样了:其一、《诗刊》是一个大家关注的地方;其二、基于历史和地位,《诗刊》一定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任何人到了《诗刊》,也只能像我这样主持。
基于中国以前的体制,《诗刊》作为中国作协的刊物,本身就代表了最高,成了很多人都想争的“公器”。《天涯》办得再好,一个学者不在《天涯》发表没关系,大家都说你是有个性的杂志,我和你的理念不合,我可以不发表。但一个诗人没在《诗刊》发表过作品,在社会上就没法混了。《诗刊》是人人都想要上的,哪怕是反对《诗刊》的人,其实心里也很想上《诗刊》。今天一些骂《诗刊》的人还是会把在《诗刊》发表过作品当回事的,他还会很津津乐道发表的事情。
《诗刊》代表着“主流”,“主流”这个词就是“不约而同”——大家不说但知道代表着什么。我刚到《诗刊》时特别谨慎,注意维持平衡,比如说要考虑刊发诗人老、中、青的均衡,也要考虑各个地方、各个民族,考虑的东西非常多。
2014年,在我到《诗刊》前,《诗刊》已经不是核心刊物。我不是替自己辩护,只是江湖上有个别人特别恨我,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正好处在《诗刊》主编的位置,很多人会把批评集中到我个人身上,认为我身上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状况。心态上,我从未将对中国新诗的批评视为对我个人的批评,而是视为对中国现代性的讨论。我对这些批评没有时间、精力和办法对付,我只能靠自己境界的提升和工作的努力来解决。
02
我不是动不动就改变的编辑,在《天涯》我做了近十年主编,《天涯》封面和所有栏目我都没动过,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风格。这几年,《诗刊》内部没什么特别调整,因为栏目只是栏目,重要的是怎么编辑它。我刚找到平衡的方式。这两年,疫情让我有了转变,我还是想把自己的新理念贯彻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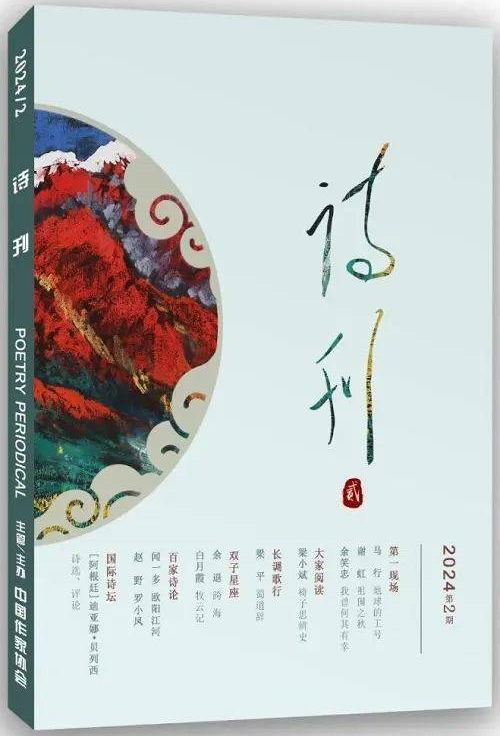
《诗刊》2024年第2期封面
我现在的方向是通过做专题的方式维持平衡,我准备每年出两到三个主题性或专题性的专辑,这代表了我美学上的推崇。我会根据上面的要求,保留主流的部分,通过专辑来弥补具有锋芒的东西。这样做平衡。平衡不是靠平庸,是靠对话或者交流,就像你不能靠讨好一个人得到认可,只有当你们水平相当,他才会认可你。
我做了“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散文诗”“自然写作”等专题。当《诗刊》敏锐地感觉到创新的力量、变革的力量出现了,感觉到能提升中国诗歌的力量出现了,《诗刊》就去推动它。以前,杨键、雷平阳能够获得影响力当然有很多因素,实际上我一直推他们的作品。我现在可能会用主题或者专题的方式来推出这些作品。
《诗刊》推出“北大女诗人”专题,就代表一种预兆,即女性的文学,与男性主导的文学不一样。至于后面的理论工作,还要更多的人来参与。我认为“女性写作”是未来的方向,这个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很明显。重要的是,这两年北大的女学生诗歌确实很优秀,比如张慧君、杨碧薇、周瓒、康宇辰,她们的才气挡都挡不住,作者都是有明星气质的。“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很受欢迎,好几个出版商约书,编一本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
通过专题,我对西方诗歌体制和中国诗歌体制进行了综合。我在编杂志做对比时发现了一个现象,西方没有那么多文学刊物,西方的诗人是伴随着一本主题诗集的出版而出名的。比如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Veinte Poemas Amor Cancion),这是一本小诗集。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每一本都有很明确的主题,比如《龟岛》(Turtle Island)是关于禅宗的,《砌石与寒山诗》(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是对寒山诗的改写。中国诗歌体制有一个问题:杂志太多,发表太容易,基本上只要写就能发。诗人很少就一个主题深入挖掘,没有《荒原》(The Waste Land)那样的作品,这是我们一直对当代诗不满的原因。我和胡弦说,你专门写大运河,一本诗集全部写大运河,写得好一定会成为你的代表作,单靠一两首诗肯定不行。《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有特别好的诗,也有一般的诗,特别好的那些诗就流传开了。但如果不是一整本诗集,个别的诗作不会带来大的冲击,达不到效果。所以,《诗刊》也专门做主题诗集,沈苇的《诗江南》、胡弦的《水调歌头》、林莉的《跟着一条河流回家》等,证明很成功。
03
我把中国的诗歌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向外学习的阶段,新诗的现代性本来就是向西方学习来的。
第二个阶段是向内寻找的阶段,一批有思想的诗人对传统进行了重新挖掘,产生了“寻根文学”。当时社会面临的问题是,诗歌的繁荣没有普及化的基础,大家都不读诗,一个人孤零零地读,怎么可能是伟大的文学时代。伟大建立在量的基础上,就像金字塔有庞大的基座才有顶尖。
第三个阶段,“手机文学”,它开启了诗歌的“民主化”。随着网络、博客、微信、小红书等的发展,诗歌的民主化和普及化程度加深。当然早期的互联网写作鱼龙混杂,作品也比较稚嫩。
民主是博弈的结果,未必是普遍的民主,而是说,在舆论、智识等方面博弈后的民主。为什么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推崇余秀华?因为她浓烈的情感打动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诗歌的“民主化”使大家都能够辨识出真正伟大的诗歌作品,能够对特别好的作品达成共识。
民主问题很复杂。为什么杜甫后来成为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诗人?这与理学占据上风有关,理学要寻找一个“形象代言人”。如果后来中国文化不是儒学,不是理学,杜甫也不会被认作主流的诗人。应该说,个人与时代或者诗歌与时代存在内在的一致性,而历史的内在一致性是很难把握的。
在社会思想层面,T.S.艾略特就像杜甫、韩愈,为什么艾略特成了西方新的现代性的开创者?因为艾略特有一种统合能力。艾略特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满怀抱负和雄心,想重建秩序——建没建成是另一回事。就文学而言,艾略特不见得是最好的,西方是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社会,他的影响力可能和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实际上,博弈后的民主也不是我能促成的。我现在能做的是,以专题或专辑的方式把有创新力量的作品推出来。
现在是第四个阶段,类似于盛唐,诗歌界没有命名,真正的繁荣恰恰是没什么命名的。盛唐人也没觉得他们的时代多么伟大,是后人总结和命名了盛唐。初唐有很多争论,“初唐四杰”之一陈子昂就一直批评主流诗坛。盛唐没什么诗学争论,大家各写各的,伟大的诗就出现了。
04
今天社会的状况与诗歌的状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一样,我们身处这个变化中,情况还看不太清楚。第三代诗人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已没有多少创造力。从诗歌史来看,第三代写诗多靠蛮荒之力、才华、青春的力量,整体续下来的不多,很多诗人的后续作品明显不如青春时期的作品。
第三代稍微往后的这一波,比如陈先发、胡弦等,还处在往上走的状态,他们还有潜力和空间。他们都在积累,等待着新的超越。但是,他们面对的困难是多方面的。
更年轻的一代人就类似杜甫,会越写越成熟。这就有点像“初唐四杰”和盛唐时期诗人的区别,“初唐四杰”写诗就是靠青春才华。年轻一代的诗人,一般有较好的学历、语言、文化修养,只是处在有待完成的状态,能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要另说。
鲁迅和曹雪芹在从事写作前,文学修养已足够,突破了,写下伟大的作品。能不能成为鲁迅和曹雪芹,这其中有神秘色彩。曹雪芹如果没有家道中落,很可能就是个花花公子,是个社会文化名流,可能不会下决心写作。鲁迅如果没有家道中落,可能是个爱好文学的医生,也可能不会下决心写作。包括我自己都能体会到,要不是我被关在家里面,什么都放下了,也写不出文章。不然,我可能天天去组织活动,没时间也没办法系统思考。
我以前有个观点,中国现代性实际上发端于新诗,新诗革命产生了中国的现代性。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完成,可能要等中国现代性的完成;反过来说,中国现代性完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也完成了。就像中国各方面都面临着各种批评与争论,中国诗歌也是一样。只有理顺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国诗歌才能达到成熟;反过来说,中国新诗达到了成熟,中国现代性问题也差不多就理顺了。现在中国现代性、中国诗歌还处在争斗或者纠结的状态,有争论很正常。
国家强大时,文化魅力也就产生了。国家和人是一样的,就像人的言与人的行是一致的,国家的文学、文化与国家本身也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文明为什么广受推崇?因为中国全方位的发展。盛唐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有那么多外国人在朝廷中任职,他们被中国的文化迷住了。

《天涯》杂志封面设计风格很统一
05
2003年,我提出了“草根性”概念,后来几年,主要围绕“草根性”做了一些工作,包括系列评论、编辑诗歌选等等。当时我在《天涯》以相对边缘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和诗歌的发展情况,我们也经常有批评主流诗坛的冲动,不过没有表现出来。
“草根性”和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关,首先是教育的普及化,其次是新媒体的发展。余秀华之所以能够出现,正得益于教育的普及化和新媒体的发展。余秀华虽然没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余秀华情感浓烈,情感浓烈与她的身体状况有关,得不到变成了幻想、想象,读者第一时间就被打动。
很有意思的是,最初喜欢余秀华的读者,是一批学历挺高的、非文学专业的知识分子。有次北大法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余秀华的诗,准确说是转载《诗刊》,之前这个公众号从来没推过文学,更不要说诗歌。转载席慕容、汪国真可以理解,余秀华当时还没出名,说明他们真喜欢余秀华的诗。大家普遍缺爱,突然有个人敢这么表达也挺吓人的,弥补了人心理上的需求。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我昨天还碰到个人,她说余秀华真厉害,这么大胆,她很羡慕但不敢。
江非、杨键、郑小琼,他们出道时都属于底层诗人、草根诗人。江非是农民,杨键是下岗工人,郑小琼是打工妹。只是后来他们进入体制,身份发生了变化,有的都当上了主席、副主席、文学院院长。这是“草根性”的第一种情况。反倒是黄灯她本身的职业和身份并不差,有更多的“底层关怀”,有更多的“草根性”。黄灯就生在韩少功现在所住的那个村,她经常跑去韩少功家,受韩少功的影响很大。我在《天涯》时还想把黄灯调到《天涯》。这是“草根性”的第二种情况。其实,李白也是草根诗人,他本“陇西布衣”,但作品里有一股野蛮的力量,好像来自蛮荒之地的文学力量。
为什么世纪初的底层诗人、草根诗人更有力量感?那是一个对抗性的时代,有一种紧张感或者对抗性。比如当年的郑小琼,她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她的作品保留了一种对抗生活的紧张感。陈年喜也是。现在社会普遍比较固化了,这种诗人已经很难出现了。
每个时代都需要“草根性”。个人的情感要转化成集体的精神,一定有更高的关怀、更大的境界,有大道大义,“草根性”就是“大道大义”。“草根性”对文学非常重要,文学除了关心自己,还关心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文学作品一定是渴望交流和传播的,不然像卡夫卡写完烧了就行——卡夫卡最初准备把自己的作品烧了,但后来他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共鸣,两者并不相同。如果你真的认为文学属于个人,完全没必要交流和发表,从事文学的人一定渴望读者和知音。
不过,我个人以为,现在还要靠学院的力量,学院有很好的修辞。但是,学院也要有变化,要走向更大的社会、更广阔的世界。也许年轻的一代人可能会有新的变革性力量,但是他的生活一定要有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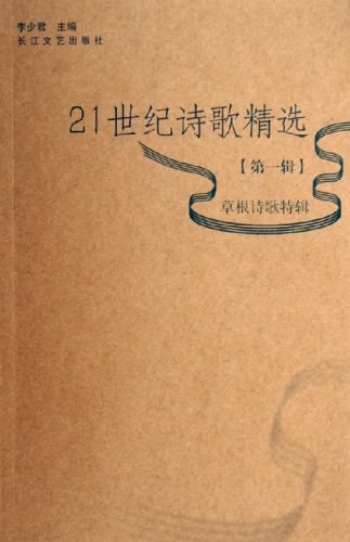
李少君主编的《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06
年轻人总是会把主流的东西当成反面。我当时在《天涯》也是这样,《天涯》的定位就是“边缘、先锋、底层”,Frontiers的英文就有先锋、前哨、边缘的意思。《天涯》的办刊理想之一就是文学栏目要尽量地面向新人和先锋性。我们判断主流作家肯定把最好的稿子给了《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天涯》是一个新办的刊物,没有优势,主流作家的第一考虑不是《收获》就是《人民文学》。我们的策略就是培养青年诗人和青年作家,葛亮、艾伟、刘亮程、张楚、叶舟、肖江虹,以及现在很多省的作协主席,比如李晓君、沈念,他们的成名作都发表在《天涯》上。
我也能理解年轻人把《诗刊》当成自己的对立面。现在我找到了弥补的办法,来《诗刊》后我就做了120位“90后”诗人选集,后来我开始有意识这么做。我现在主编的《诗刊》,下半月的内容就体现了我当时在《天涯》的办刊方向,上半月编发的是相对比较主流的诗歌。2024年上月刊和下月刊合刊后也保留这个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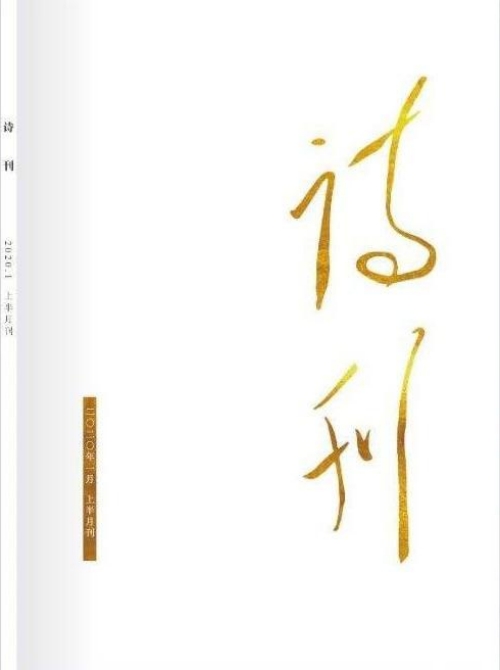
《诗刊》2020年1月上半月刊封面
总体来说,现在这个时代的对抗性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以前整个社会相对封闭,突然有一种撕裂,对抗性就比较强。现在很平静,也有选择的自由,我不喜欢我就换一种生活环境。也不排除若干年后回过头看,现在恰恰是憋着默默努力的时代,很多人在积累在沉淀,等下一个阶段突然爆发。历史上大的事件产生前一般都风平浪静,比如法国大革命爆发前。
年轻一代的好处是,能够在良好的基础上进行整合、统合。从今人的眼光来看,杜甫视为榜样的诗人都不如他。杜甫苦学“阴何”,就是阴铿和何逊,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阴铿和何逊,他评价李白写得像阴铿,他自己认为这是很高的评价。
先积累,再不断自我超越。现在需要的不是开拓新的题材,而是要达致新的感觉与思想,获得新的消化能力和统合能力,也只有真正强大的心智才能整理如此庞杂的材料或者现象。如果完成了这个过程,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诗学观,乃至于一种新的价值观。
07
我现在老谈诗教,对诗歌的推崇近乎宗教,投身生活,生活就会回报你。我写海南的诗歌大都是现在写的,到北京后写的,在海南时我写不出来,当时觉得辛苦。苦难,现在反而有了诗意。这就是历史逻辑的特点。历史无情,但时间能净化,能解脱所有苦难的人。
诗教关注的更多的是精神问题、心灵问题。我之前说过,我经历过哲学和社会学两个阶段,现在我觉得心灵的、精神的阶段更有普遍意义,更能得到认同或共鸣。伟大的诗歌,就像《唐诗三百首》里的一些诗歌,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还会打动读者。可以想象我们这个时代的争论在历史上也都有过,李白、苏轼都卷入过很多重大的政治争论。一些历史上的争论,慢慢就变成专业问题,未必有人会记得。但是心灵范围的内容(他们的文学作品)关涉到文明史,关系到人类普遍感觉、感受、思想,可能会更长久。
中国古代文化中,文史哲是不分家的,诗教作为最基本的教育方式。孔子认为,《诗经》恰好包含了一些他认可的价值观,他把《诗经》排在第一位。为什么杜甫那么被推崇?第一,他的诗好;第二,他最符合儒家理想,忠心爱国、忍辱负重、牺牲自我。
而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诗教是一种修养,其中蕴含着的价值观具有宗教的作用。马修·阿诺德有个类似的观点,在“后神学时代”,诗歌可能会成为一种准宗教。中国本来没有宗教,这一点就更突出。诗教就是关于人生修炼或者境界提升的一种思想哲学。
我特别认可“境界说”,“境界说”能够让你不断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冯友兰特别欣赏“境界”这个词,我理解境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心灵品位或者精神等级。当你身处一楼时,你看到的事物是有限的,到了二三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境界越高,看到的越多,包含的越多。
里尔克提出“诗是经验”,所谓经验就是沉淀的情感,经验没有情感是记不住的。举个例子,你肯定不记得多少小学同学,因为情感没有沉淀,交集不够。只有当你喜欢他、讨厌他,你对他有更深刻的情感,经验才能变成经验。没有情感的经验不会成为经验,沉淀了情感的经验才能成为经验。我们就从“诗言情”过渡到了“诗言志”。“诗言志”是精神的标准。
为什么历史上那些伟大著作能够永恒地流传下去,这些著作蕴含的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精神。情感和精神是不一样的。“志”是理想、价值,是大道、大义,它才能成为精神。作品如果只有情,可以打动人,可能会流传,但不能跨越时代。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情感,但要成为精神性的存在,一定超越了个人的情感,像古人所说的天地境界。
疫情期间,我天天在家读书,和庄子、老子、苏东坡、李白对话。他们的精神力量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做不到的,要达到他们的状态,一定要把情感转化为精神性的力量,这种精神性的力量可以穿越任何时代。

李少君在北京大学做讲座
08
我现在经常遭受各种攻击,我对别人开玩笑说:你想想看,在古代写首诗,要不就被流放,要不就被砍头,我们现在只是被骂,还能继续写,还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幸福了。所以,重点还是热爱生活,真诚生活。我当时投身《天涯》,关心“三农问题”,关心生态问题,关心WTO,都是很真诚的。我真的认为,这些问题会对国家、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更长的历史看,历史本身有其内在的规律和逻辑,不会因个别人有所改变。我们的争论其实可以有,其实也可以没有。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楼台,最后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四大名楼。只有文字,只要有诗歌,黄鹤楼可以不断地被烧,不断地重建。这就是文明。诗在,黄鹤楼就在。
我最近去绍兴兰亭,就是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地方。据说,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把真迹带去陪葬了。科学技术受限尚不能进入墓地,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所有在世的《兰亭集序》都是临摹的。清康熙帝特别推崇《兰亭集序》,就临摹了《兰亭集序》,并在兰亭刻了碑。康熙的孙子乾隆也特别推崇,爷爷立过了,乾隆不敢僭越,就在兰亭刻碑上写了另一首诗。这说明,诗或者文字是高于所有东西的。但你要亲身经历过,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否则只拥有纯粹的思想、纯粹的理念。
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诗,往往比历史更真实。陈寅恪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他说《唐史》里许多想当然,错误甚多,时、地、人的关系混杂不清,难下结论。唐诗却是清楚地谈到时、地、人,谈到人的感情、关系,融成一气。故诗有史之意义。杜甫诗就被誉为“诗史”。
明末王夫之在家国大变之际,藏于深山,系统地对传统诗歌审美做过梳理总结,在强调“情景交融”的基础上,提出“情、景、事”三者交融,他说:“一时、一事、一情,仅构此四十字,广可万里,长可千年矣。”诚哉此言!诗歌,既是个人情感史、心灵史,也是生活史、社会史。这也是“人诗互证”传统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原因。
09
1995年,韩少功创办《天涯》杂志,当时我是他的兼职编辑,编的第一个栏目就是关于诗歌的。1996年《天涯》第四期专门编发了“诗歌精选”,每年一期“诗歌精选”保持到现在。我不太关注已经成名的诗人,关注同龄人。我编的第一期“诗歌精选”选的十位诗人都是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龄更小的:陈先发、杨键、侯马、伊沙、臧棣、小海、凌越。凌越那时可能未从华东政法大学毕业。
第二期推出了多多的专辑。多多出走海外之后,我是在大陆第一个推出他的诗歌的。当时国内读不到多多的诗,我看他在海外写的一批诗很惊讶,就向韩少功推荐。韩少功说可以,但最好配篇评论,好多人不了解多多的情况。我约了黄灿然写了评论。
在我看来,多多、昌耀等代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最高水平。我一直认为,多多是当代诗里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这个判断从没有变过,一以贯之。从诗意上来说,当代没有人写得比多多更好。现在我还选多多,2021年的“屈原诗歌奖”,我第一个就投给了多多。多多性格很怪,但他有自己的坚守,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特别,其他人还真做不到。
多多是后来来海南的。当时他在荷兰,跟我说想回来找个工作,我就找了耿占春和萌萌,他们去和海南大学校长说,这样他就来海南大学当外籍教授了。多多来海南后,有一批诗人开始汇聚在海南,多多、耿占春、徐敬亚、王小妮等,诗歌活动也多起来了。
第三期、第四期的“诗歌精选”推出了雷平阳、江非、辰水等年轻诗人,我主动组稿约和自然来稿中选的,雷平阳最著名的诗基本都发在了《天涯》。
因为《天涯》议题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生态和文化等,我曾和很多教授、专家都有联系,以致文学界曾有一个说法,说要找不到人,问李少君,没有他不认识的。当然这个有些夸大,但当时和全国文史哲等各学科的学者都有一些联络。我也因此经常参加国际国内的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和论坛,包括亚欧人民论坛、世界和平大会等,也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
即使如此,我与诗人的交往和对诗歌的关注从未间断,只是有一段时间去写小说和随笔了。1996年,我能够在《天涯》一开栏目就编发诗歌,也与一直跟陈先发、伊沙、侯马、西渡、臧棣、凌越等保持联系有关。我诗歌阅读量很大,交往的诗人会把诗集寄给我。有一段时间大家不太写诗;第一是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要熟悉工作,还有成家立业的压力;第二是一个人有段时间不写很正常,创作灵感和高潮不会一直持续,是一阵一阵地,不写并不意味着没有在读、在思考。

李少君和陈先发、胡弦、汤养宗、刘笑伟、曹宇翔、田禾等在江西横峰乡村
10
1990年代后,国人对社会急剧的两极分化都有切身感受。那时大量工人下岗,突然都没工作了,有的被迫“下海”,有的做非法生意。农民的生活状况也很糟糕,肥料等上涨,种地不仅不赚钱,还会亏本,不少农民被迫到城里打工养活自己,这就是“三农问题”。由此,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底层问题。
以我家为例,我父亲原来在政府机关工作,待遇并不如工厂。八十年代初,我家比较困难,父亲身体不太好,三兄弟年龄相近,都在读书。姑妈家在国有大企业工作,条件比较好,是我们当时特别羡慕的。1990年代后,姑妈家经历了下岗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越来越糟。
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最早敏锐地察觉到贫富差距问题。蔡翔在《上海文学》当主编,后来又去上海大学任教,他比较早地注意到工人和他的生活差距越来越大,感到良心不安,他原来在工厂工作,所以认识很多工人。蔡翔是较早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知识分子,写了《底层》这篇文章。海南作为开放的特区,贫富悬殊比别的地方更大,1990年代初海南的房子就有一万多块钱一平米的,当时北京、上海也就上千,我们在海南更能体会到这种差距。
客观地讲,我们讨论底层写作与社会现状有一定的关系,应该呼吁大家关注底层,但不能让社会破裂或崩盘,按照当时说法,就是要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真的发生了动乱,对大家都不好。
为什么当时《天涯》的影响那么大?是因为把出于知识分子立场感受到的社会问题都提出来了,“三农问题”、生态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天涯》是比较早讨论生态问题的。有段时间,有些地方为了挣钱,建化工厂,水源被污染,牺牲了大家的健康。后来中央发现生态问题,开始整顿。当时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读书人本能的良心不安,或者说对这些问题的负罪感,希望引起整个社会关注。
11
进入《天涯》不久,我进入社会学的阶段,关注社会问题。我积极主动地参与过社会活动,比如给农民办班。同时我开始大量地阅读社会学、经济学的书籍,甚至比较系统地读过包括讨论宪法、刑法、名誉侵权的法律书籍。我也是较早关注生态问题的,写了大量随笔讨论生态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把我视为自然作家。
《天涯》组织过很多知识分子讨论生态问题,包括汪晖、黄平、王晓明、陈思和、苏童、格非、戴锦华。当时《天涯》参与过很多重大的讨论,比如说关于加入WTO,虽然中央决定要加入WTO,但反对的声音也挺大,《天涯》把支持和反对的意见都刊登了。
社会学有个问题,双方的意见理论上都可以自圆其说。关于加入WTO的讨论,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是右派的思想,右派认为太好了,加入WTO就进入了世界体系,开始真正地向西方学习,变得和西方一模一样。另一派是左派的思想,左派认为不能加入WTO,加入后就会被西方绑架,沦为新的殖民国家。
回过头来看很有意思,双方的预想都没有实现。第一,中国加入WTO后,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国,变得强大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GDP增长了无数倍,接近发达国家。右派的理论没有实现,党和国家更加自信了,更不可能和西方国家一致。左派的观点也没有实现,中国不仅没有沦为殖民地国家,现在还拥有了话语主导权。
我以杯子为例,我们俩坐在这里讨论,从你的角度看,杯子上是有字的;从我的角度看,杯子上是没字的。我们相信自己所看见的,一直争论这个杯子上有没有字,你认为有,我认为没有,但实际上我们都没有看到全貌。这种社会学的争论是有问题的,短期内你的观点可能会占上风,但也可能会反转,我的观点也有可能压倒你。现在社会中的争论就是这样,一会左一会右,一会东一会西。
12
年轻一代可能更喜欢西方,迟早还是会返回中国文化。年轻人有逆反心理,可能以前越喜欢的,有段时间就越反叛它,但最终会回过头来。就像现在美国“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已经成为美国精神的代表,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基本上成了最主流的美国诗人,因为他曾经反叛给主流增加了新鲜的事物。没有反叛就没有加里·斯奈德。
但根本性的东西很难改变,因为所有人自小都沉淀过诗教的基础。我们年轻时也一样,有段时间几乎不看中国书,看的全是外国小说,就像有段时间热衷吃西餐,上了年纪后还是吃中餐。我以前每次出国差不多都待了半个月、一个月,吃西餐,刚开始还很新鲜,感觉西餐味道很好,吃到最后天天找中餐馆,实在吃不惯西餐。文化就像这样。只要从小读的是中文,学的是唐诗,就打下了基本的底子,我不担心“中国性”的匮乏。
当时很多人想获得西方的认可,但是观念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变得强大,我那一代就不再满足于西方标准,不再满足于获得西方认可,我们重新寻找中国性的命题和内容。今天年轻一代普遍修辞能力很强,但是能不能成为鲁迅或者曹雪芹,有神秘的力量主导,或者说一种你说不清的时代的力量。这需要一个过程。
外国诗歌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简言之,用中文表述就是中国诗歌。只要被翻译成中文,这些外国诗歌就能成为中文、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经过卞之琳、穆旦的翻译、改造,这些外国诗歌已经被转换和吸收,就像翻译的佛教经典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一样。
青年诗人了解西方后可能会更了解中国。好的东西是比较出来的。一个女孩,你印象不错,另有一个女孩,你能比较出谁更漂亮,三个女孩,你也能比较出谁更漂亮。文化也是,刚开始是西方文化这个女孩,你觉得她好,等第二种文化、第三种文化,你才能比较出谁更如何。当然你有真的雄心和抱负,渴望成为大诗人,你就有这个问题的自觉。我不担心,我相信年轻一代会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西方汉学界还在寻找热点,目前受西方汉学界欢迎的,比如郑小琼。西方汉学界认为,中国还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很重要。还有北岛等诗人,有政治标签,符合西方的需要。但与之相比,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读诗写诗,是希望获得一种精神的提升,所以首先是个人的问题,其次才是外在的影响,比如获得读者、市场还有所谓国内外的认同,如果没有这个,可以说就失去了初心。